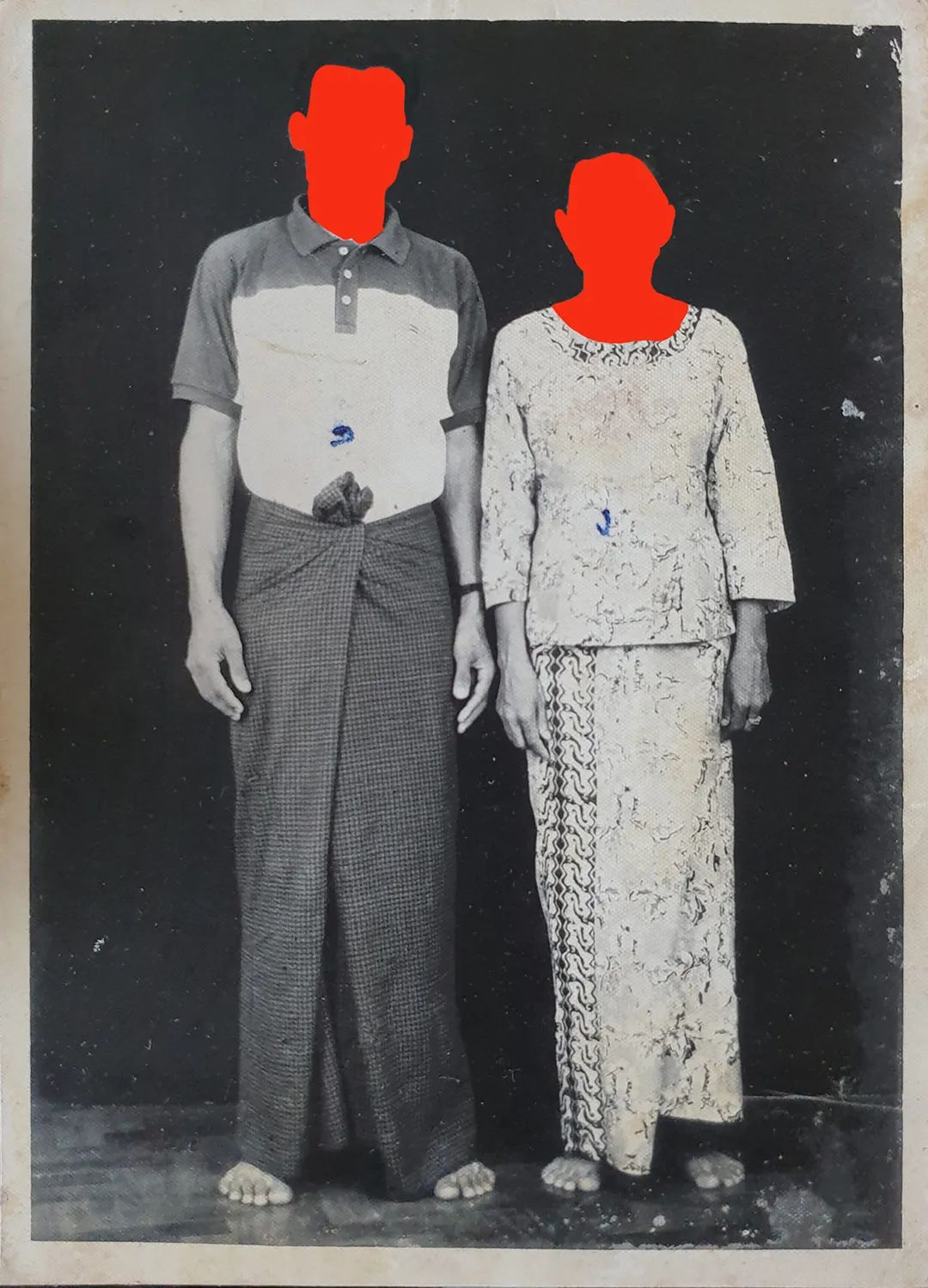2 min to read
Pronoun不正确|从“他们”到“我爱你”,东南亚代词的温柔错用
当代词不再只是指代,而是一种触碰——我们邀请你,从词语的缝隙中写出属于你的温度与偏离。
关于代词的争论,常常被归入语言政治和身份正义的范畴。但这次,我们试图跳脱这样的框架,转向代词在东南亚语境下的流动性实践——它们如何在历史、结构与权力中折射,又如何在缝隙中被轻柔地使用?这不是一次对“更正确”的代词标准的追寻。同时,我们希望开启一次征稿邀请:让我们在语言尚未闭合的空间里,创造一种代词诗学的写作可能性。

起初只是一个标题。
那天晚上,“交错带”的伙伴们正编辑着《双城记|离散的人不想家》(原标题《双城记|他们说自己不想家》)一文时,有人提出了异议。
“题目的‘他们’要不改成‘Ta 们’?”
这个简单的句子砸入群里后,是一阵沉默。
接着有人提出了“汉语历史主义”的主张。
“我主张抢夺对‘他’这个词的重新定义,‘他’是一个单人旁,代表的就是普遍人类,从来不单指男人。我们未必非要照搬那套英文语法的性别表达方式,也不是非要用拼音字母来显示友好。”
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汉语历史主义”,“他”字已经被默认是男人,哪怕它曾经中性,现在也不是了。所以在现在的普通话语境里,‘他们’一词说到底并不真的中性,它默认了性别权力结构。
争论往下延伸到代词的构造本身。有人说:“我希望活在一个没有 pronoun 的世界。”
这确实是一个麻烦,这世界的代词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像标签管理。他们气质、她们气质、非二元气质、queer 气质——我们拼命命名、分类,可最后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再度加标签。只要我们还在用英文去想象代词的革命,就会把自己绕进另一套结构之中。这究竟是流动还是凝滞?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并不只是一个词的争论,也是我们试图看向语言的交错带。可是语言是否愿意留给我们这样的位置?还是,它早已成了一张太过整洁的地图?
代词的赋权与清洁暴力
这场关于代词的争论中,焦虑并非无的放矢。代词,作为语言中最小的分类单位,往往最先暴露出语言背后的权力线索。中文的“他”与“她”并非自古就如此分工,而是近代的翻译浪潮的推动下,被人为切割出了一对性别对偶。
黄兴涛在《“她”字的文化史》中指出,早在 19 世纪初,出于翻译英文“she/her”的需要,“伊”这个原本中性的第三人称代词开始被女性化,承担起性别指代的功能。但如果将视线转向马华文学或福建一些地区方言,会发现“伊”字至今仍在使用,依然是一个未被性别训诫的中性代词活体。
到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中,“伊”显得格格不入。有人开始用“这女子”、“那女子”等等冗长句式来解决性别代词的缺席问题。直到 1920 年,刘半农写作了一首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这是“她”字的第一次出现。
然而在当时,这一创新并未得到一致认可。即使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人,也对“她”字的发明存在激烈分歧。百年后,“她”字扎根日常,这场争论既被部分验证,也显现出错位于时代的复杂。而语言的性别秩序,确实就这样在一番现代化的权衡中,悄然立起。
英语世界近年来大力推广 they/them 作为非二元代词指代“he/she/him/her”,语言似乎终于为一个更流动的性别世界松动了一下。这次运动赋权了非二元群体,2015 年美国语言学会也认可 they 作为单数代词。中文世界也很快响应这场动员,借用拼音“ta”来当作一个中性指代。但这种松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洁运动”——背后是一套新的规训,一张更细的筛选网。
演员 Nico Tortorella 在 2024 年公开把自己的代词从 they/them 改回 he/him,结果立刻遭遇批评。他原以为代词可以随关系、情感的变化自由流动,只要它们有利于交流的顺畅。但部分公众却愤怒地认为他的做法是一种倒退。这种事情几乎是撕开了“they/them”作为性别友好的面具,你可以自由加入,但你不能退出,否则就是叛离。
更早以前非二元作家 Andrea Long Chu 表达过对这种代词政治的警惕。她指出,“询问代词”被当作一种社交礼仪,其实常常只是“风险管理”——它压缩了性别本身的复杂经验。不是为了理解彼此,而是为了免责。于是,我们不承担彼此的复杂性,只在履行一种不犯错的语言程序。
“我爱你”,可以是一次美妙的性别滑动
在这场讨论陷入二选一的抉择时,有人轻轻说道:“你们知道吗?泰国人会出现混用男女代词的情况,比如女性在吵架时会用男性的人称代词 phom 来表达强硬态度。男性用女性代词的时候是表达比较深情温柔的语境,比如唱‘我爱你’的情歌。”
这句话开辟了新思路,有人立刻回应自己遇到的相似经验:“缅甸人的第一人称代词也会分男女性别,男性是“ကျွန်တော်”(kyá.nau),女性是“ကျွန်မ”(kyá.ma),但不知道为什么曼德勒的女孩从来不区分。所以我一旦听到缅甸女孩子用的是男性代词自称,我就知道她一定是来自曼德勒。”
这些语言的实践令人兴奋,好像打开了一扇窗:语言原来也可以不那么分类,不那么规训。这些声音也唤起了我们一种模糊的浪漫想象——“如果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指代和描述都只是形容词和动词就好了。”泰语这种人称代词高度情境化的使用方法似乎就成了一种性别自由流动的可能。或许有某些语言经验,它本身就是流动的、错位的、无须新增命名就能表达差异的……
在泰国流行音乐中,“ฉันรักเธอ”(chan rak ter,即“我爱你”)常由男性歌手唱出。他们用的是女性第一人称“ฉัน”(chan),唤着心爱人“เธอ”(ter,亲密但性别中性的“你”)。当男性说出“ฉันรักเธอ”的时候,他仿佛以一种女性柔软的身态,缠绕出内心秘密的情愫,向对方伸出情感的触角——语言真正抚触了身体,它不是什么宣言,而是亲密情境下的自然滑动。
在泰国的 queer 社群里,代词几乎是一块可以随意剪裁、拼贴、上身的布料,这一点 Peter Jackson 有深入的观察。gay 男性与 kathoey(跨性别女性)在代词使用上展现出不同的方式:gay 男性灵活切换阳刚与女性化代词以适应语境,而 kathoey 则偏向用女性化语言以强调女性认同,却也可能在亲密互动中借用中性代词。他们不急于锁定身份,而是在社交中策略性地调度代词,转化为多变的性别和情感风格。
比如公开场合或面对陌生人时,大多数 gay 男性会使用正式男性代词 “ผม”(phom,我),结尾加上男性敬语 “ครับ”(khrap),这种标准“男性”格式是他们在社会舞台穿着的一身西装;而回到熟人圈中,代词就开始偷换气味。为了表达柔媚气质,他们会使用女性化第一人称“ฉัน”(chan)或“ดิฉัน”(dichan),私密时使用中性的“กู”(ku)——一个粗鲁却亲切的第一人称代词,像姐妹之间的互呛。
这套代词系统不仅关乎“我怎么称呼自己”,还延伸至如何称呼对方与谈论他人。gay 圈中常用 “หนู”(nu,原意“小老鼠”,通常由年长者对年幼者使用,带保护意味)表达亲昵;也会以 “หล่อน”(lon)、“นาง”(nang)等女性化第三人称代词来互称朋友,建立一种“姐妹话语”的幽默场域。而在强调阳刚气质时,则会用 “เขา”(khao,中性代词“他”)来塑造另一种风格角色。
这些代词的错位藏着颠覆的火花。Judith Butler 在《Gender Trouble》中提出,性别并非本质,而是一场通过语言与行为重复的表演。泰语代词的游戏化错位嘲弄了 phet 话语的异性恋规范,暴露规范的脆弱性,Peter Jackson 称此为“在地酷儿化”。相较于英文 they/them 的政治化诉求——重塑身份的宣言,泰语对代词的叛逃更像一个精巧的即兴舞蹈,重新编织性别的可能性。
不过,英文 they/them 的非二元浪潮,是否在泰国的语言缝隙中激起回声?如上文所说,泰语复杂的代词系统本身就具有表达中性的潜力。比如“กู”(ku,我)、“คุณ”(khun,你)、“เขา”(khao,他)等等就是一个个现成的中性代词,但在泰国在地社交的情境中,它们的使用往往并非为了回应非二元身份政治。
这些性别角色的嬉戏精彩纷呈,正因如此,在最初面对这些经验时,我们确实曾产生一种浪漫的猜测:代词是否能完全模糊性别,轻巧、柔软地流动?然而,越深入语言结构的考察,却越发现这些“轻盈的错位”本身仍然嵌套在高度社会化的语法秩序中。

语言也许没有中立带:泰缅代词秩序
当我开始认真检视泰语和缅语中代词的使用逻辑时,那种最初带着浪漫想象的兴奋感逐渐转化为一种复杂的理解。的确,这些语言中代词的使用呈现出流动与错位的现象:男性使用女性代词以表达温柔、女性在表达愤怒时借用男性代词、缅甸曼德勒女性普遍使用男性自称。但这样的语言并非全然中性,它们仍处于高度社会等级化的结构中。
泰语代词系统极其复杂,不同的代词使用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亲密程度、场合正式性密切相关,它们塑造了什么是“得体的说话”。不同于现代西方代词性别政治诉求的是,泰语的代词更侧重于说话者与听话者等级地位、社会关系的相对位置,而非说话者自身的性别认同。
泰语中,“ผม”(phom,男性“我”)与“ฉัน” (chan,女性“我”)不仅承担性别区分的功能,更是语气和社会情境的修辞工具。phom 的原意为“头发”,在泰文化与佛教观念中,“头部”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被视为一种克制、体面的正式自称;chan 则源自佛教礼仪用语,巴利语原义为“供奉”或“祭品”,在僧俗互动中代表一种低位者的谦卑姿态,转入世俗语言后被用作女性自称,保留了温和与从属感的语调。更卑下的代词也在泰语中广泛存在,如 ข้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佛陀之奴仆”)为古典正式自称,简化为“ข้า”(kha)后常见于阶级色彩浓厚的文学或地方用语中;而“กู”(ku)则为粗俗语气中的第一人称,用于极亲密、对等或冲突场合,带有明显的语用张力。
有趣的是,“กู”(ku)一词并非始终带有粗俗语气,甚至是更包容的中性自称。之所以变成了粗俗的代词,正是在泰语社会等级序列逐步制度化以后,这种模糊和平等的称谓反而显得无礼了,所以把它贬斥为粗鲁/乡下人的语言。它的演化也许揭示了模糊的语言可以更包容,精细化的语言反而压缩空间。
缅语同样是等级系统严格的语言。缅甸标准语中,男性使用“ကျွန်တော်”(kyá.nau)为第一人称,女性使用“ကျွန်မ”(kyá.ma)。二者都源自“奴仆”的自称形式,是等级礼貌体系的一部分。在曼德勒,女性确实使用 “ကျွန်တော်”(kyá.nau),但根据 Müller 和 Weymuth 的研究,这并不是一种性别政治的实践,而是地域差异和历史语言变迁的结果。事实上,当我间询问曼德勒的朋友时,她也说到自己从未想过代词和性别的关系,只认为曼德勒女性使用男性代词自称是一种更为礼貌的的规范。
这种“性别越界”的语言实践,若没有明确的语义抗争背景,它本身不会构成性别意识的挑战。它被“允许”存在,正是因为它没有动摇现有的秩序。
不仅如此,在缅语中,第二人称敬语如“ခင်ဗျား”(khang bya:)和“ရှင်”(shìn)皆用于表达尊重,前者语源上更偏向对男性的敬称,后者则多用于对僧侣、长辈或女性的礼貌称呼,但两者在现代语境中使用已趋泛化,并非严格按性别划分。第三人称代词“သူ”(thu)形式中性,而“သူမ”(thu ma)作为其女性特化形式,在书面语中专指女性。这些例子表明,缅语中的代词系统并未去除性别,而是将性别属性牢牢嵌入在礼貌等级与社会角色的表达结构中。
换言之,泰语、缅语代词的灵活和丰富不等于其“自由”,反而可能隐藏更细致的、等级更深的社会秩序。我们原本想象代词可以像形容词或动词那样随着气质而变化,或如光谱般流动。但它依然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结构之外的流动工具。
那些错位、混用、借用的代词实践,并不来自语言结构的进步,而是来自社会复杂性中的缝隙,是人们在不彻底打破语法的情况下所施展的小动作。
也许我们终将无法在某种现成语言中找到“完美代词”,因为语言从不悬浮于空气,而是扎根在结构、历史与权力的泥土之中。每一种语言总带着它的秩序、盲点、沉默。我们一次次提出新代词、新标签、新分类,试图绕开性别的桎梏,却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落入另一套更隐秘的规训之中。
只是,马华文学“伊”字的保留、不同语言结构的存在,总在提醒我们:应有在语言中保留缝隙的能力。我们是否可能在缝隙中发起实践?
代词诗学:缝隙中的邀请
语言的更新是必要的,执迷于“正确语言”却未必。那些起初为包容差异而生的新代词、新命名、新划分,也可能陷入一种新的语言洁癖 —— 以为只要命名得够多、够细,就能抵达一种绝对的正义与纯洁。可这,是否会成为另一种治理?
每一次我们想说得更“对”的时刻,是否也是语言小心收紧的一刻?一只困兽,也在词语里转身。
我还是难忘那一句:“ฉันรักเธอ”(我爱你)。
在这里,代词不是立场,而是动作,一种触碰。
它不指向某种更“对”的身份,却创造出一种共在的温度。
若要让缝隙呼吸,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种“代词诗学”实践。我们邀请你加入这样的创作实验:这不是规范的重塑,而是游戏的邀请。无需追求“正确”语言,只需在词语的裂隙中注入属于自己的试探方法,以流动、模糊或游戏性的方式,书写代词的另一种可能。
你的文字可以是诗歌、随笔、短片故事、实验文本,或任何你喜爱的文体类型。
字数建议 200-1000 字,灵活为之。
如何参与:
请投稿至我们的邮箱:jiaocuodai@gmail.com
我们将精选作品发布,并尝试在未来集结制作数字 Zine,或以其他任何可能的方式分享、展出。
截稿日期:2025 年 7 月 31 日
参考资料:
- 黄兴涛. 《“她”字的文化史》[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 Mathew Rodriguez. “Nico Tortorella Updates Pronouns to He/Him.” Them, 22 Oct. 2024, www.them.us/story/nico-tortorella-updates-pronouns-he-him-bethany-meyers-full-of-shift-podcast. ↩︎
- Thora Siemsen. “Andrea Long Chu on Femaleness, Desire, and the Body.” The Nation, 4 Nov. 2019, www.thenation.com/article/archive/andrea-long-chu-females-interview. ↩︎
- Narupon Duangwises, and Peter A. Jackson. “Effeminacy and Masculinity in Thai Gay Culture: Language, Contextuality and the Enactment of Gender Plurality.” Walailak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4, no. 5, 2021. ↩︎
- Peter A. Jackson. Queer Bangkok: 21st Century Markets, Media, and Right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1990 ↩︎
- André Müller, and Rachel Weymuth. “How Society Shapes Language: Personal Pronouns in the Greater Burma Zone.”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vol. 71, no. 1, 2017, pp. 409–432. ↩︎
- Wikipedia contributors. “Burmese Pronoun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mese_pronouns. Accessed 8 May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