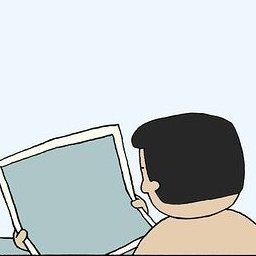2 min to read
缅甸札记|我们要如何珍视“平庸之勇”
此刻你正体验一种极度私人的共鸣,恰恰因为与人群融为一体。
Yan来自缅甸,从业于公民技术领域。他在政变后移居泰国清迈。这篇札记写于地震发生前夕,于3月24日发表于他的substack账号,原题为《选择铭记,选择遗忘》。文章将缅甸的苦难置身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加沙的平行现实之间,带出作者关于抵抗、集体创伤、技术与记忆的思考。本文经Yan授权翻译成中文在《交错带》发表,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文章某些部分我们尽可能在保留原意的情况下做了处理。可以读英文的朋友,请点击链接进入他的 newsletter页面。
作者:Yan
译者:Jiaxi
2025 年已过去两个半月,这十一周如千钧之重加身。原以为今年一切尽在掌握,但似乎每个星期都遭到当头一棒,完全措手不及。缅甸队友适逢征兵年龄不得不紧急越境;我自己也仓促跨境到老挝、办理临时签证;做了半年的志愿项目突遭驱逐;一段珍视的感情无疾而终;再加上特朗普政府撤回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直接重创了像我这样在国际发展行业工作的人——焦虑值持续爆表。尽管深知身处动荡年代,直面这一切现实还是常常让我喘不过气,远比预想的更煎熬。
本打算在 2 月 1 日缅甸政变四周年时写这篇文章,但过去几周力不从心。坦诚地说,眼下我正全力掌控局面。逆风呼啸,请稍作包容,我会尽力应对、补救,在混乱中摸索前行。
2024 年 9 月,毁灭性的洪灾席卷缅甸,让本已饱受内战摧残的百万余人雪上加霜,那时我竟莫名想写一首诗。我几乎从不写诗,也很少主动读诗。虽然很享受朋友发给我的精选诗作,但从不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某些时候,也许一年一次,思绪和感受会在我脑海中凝结为文字,感觉这些文字可以用散文以外的形式串联起来。
那时,是一种积聚的感觉,沉淀在我们身体、心脏、记忆中的,渐渐要满溢出来。数月后重读这首诗,我甚至要费力拼凑自己当初写下它时的记忆。
消逝的信息
一日
八小时
五分钟
三十秒
四年
它们已不复存在。
还要多少次
才结束?
我们一生
能承受多少负重?
水下。
火中。
注视的目光中。
距离的重负下。
要明白
我们选择遗忘
正因我们能选择铭记
选择遗忘
我认识一些从事数字安全工作的朋友,他们的职责是帮助民间社会的弱势群体建立安全的数字习惯,比方不在所有账户使用相同的密码、将数据备份到加密云端、或使用加密通讯软件 Signal。他们最常抱怨,生活中大多数事情,人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直到飞来横祸,才突然想到那些早该采取的防范措施。
2021 年 2 月政变后不到几个月,缅甸就有数百万人开始使用 Signal 处理所有即时通讯需求。没人知道新军政府掌握着何种尖端数字监控技术,也没人愿意冒险。大家终于想起了技术宅朋友们一再推荐安装的应用,据说能让你的讯息免于窥探。
如果你还没听说过,Signal 是由理想主义极客团队开发的非营利应用程序,仅依靠慈善捐款运营,且完全开源。与其他以监控资本主义为商业模式的通讯应用不同——通过尽可能收集他们的用户数据牟利——Signal 不搜集任何用户信息。
它还首创了许多后来被其他通讯软件广泛采用的功能,如“阅后即焚”。高度敏感的对话,你可以设置让聊天记录在一定时间后从手机、电脑或云端彻底消失,与当今数字世界的运行逻辑完全相悖。在这个政府、企业乃至个人都想拼命记录并记住一切的时代,我们被灌输了“错失恐惧症”,坚信人生每张照片都值得永久保存: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为什么要抛弃,对吧?
是啊。
就在此刻,德黑兰的某个警察正悠闲地看着算法,将抗议者的面容与姓名相匹配,国家记得每个人;旧金山的某个亿万富翁,则盘算着如何把所有现存记录都变成 AI 魔兽的训练素材。
但在缅甸政变初期,我们不想留下数字记忆。所有人涌向加密通讯软件,开启“阅后即焚”模式——有些对话中的信息如电光火石,每三十秒自动消逝;另一些虽持续时间稍长,也不过留存数小时;若确保所有通讯对象身处安全地带,也许能延长至一周。当数字设备承担记忆的功能变得过于危险,我们不得不重新依靠人类的记忆。

图:Khin Thethtar Latt (Nora)
人类的记忆不同于计算机。我们会为记忆赋予意义,我甚至怀疑大脑能否真正记住那些毫无意义的事物。正因如此,我们将所有经历提炼成必须留存的核心片段,以构建想要记忆的故事。此处我没有刻意区分“需要”与“想要”二词,以凸显两者的张力。有时我们的身体会违背意志,将这些记忆与故事深藏心底。身体“需要”与心智“想要”的界限,就此模糊不清。
通过巴塞尔•范德考克的《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我了解到创伤体验会事后长期潜伏于一个人的身体里,往往能绕过意识记忆。他举例:一位童年遭受虐待的女孩始终无法回忆起受虐经过,但当被要求描绘童年时,她的潜意识却掘出可怖画面——幼小的自己困在笼中,周围环绕着无眼的黑影与直指着她的巨型阳具。
作者解释道:“遭受创伤的本质,是以创伤仍在持续的方式构建生活——仿佛它永远不变——每次新的际遇都被过去所污染”(第 62 页)。你受过创伤的大脑会不断向身体发送信号,要求逃离早已不存在的威胁,就好像它真的还发生在你身上一样。身体对此的反应令人心惊:觉得周遭一切都充满威胁,只要与创伤事件有一点点关联就会触发反应,完全无法感知身体的某些部位,乃至像上面那个女孩那样彻底封锁记忆。有些烙印在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无法选择遗忘。
然而危机中总有一线希望,无论多么微弱。政变大概一年后,我与缅甸友人的对话总会自然转向心理健康与创伤话题。人们坦然分享看心理医生的经历,以及他们获得精神支持的体验。这些曾经在缅甸社会讳莫如深的话题能被如此公开讨论,让我看到了走向集体疗愈的可能。
俗话说“往事一笔勾销”,但我仍弄不懂这笔应该落在疗愈的哪一章?原谅与遗忘该是什么先后顺序?我既期待又担心:大家会为了继续好好生活而选择遗忘。如果这样做,将来回望时,是否可以原谅自己?当我们早已不复存在,那些主动选择遗忘的事物,是否仍会在我们的躯体、技术、社群与社会结构中留下烙印?
选择铭记
最近出于偶然的契机,我对一段特殊的历史感到着迷。机缘巧合下,我开始研究中国革命与印度支那后殖民战争之间的千丝万缕。只要是无法美化西方形象的历史关键部分,又或者他们并非主角的地方,资料就鲜有记载,至少英文如此。太过分了。所谓值得铭记的历史,很少能平等地衡量生命价值。数据显示,某些国家内战死亡的人数高达九百万,相当于二战所有轴心国的死亡人数总和;而六七十年代美国在弹丸之地老挝投下的炸弹,超过了其二战期间的总投放量。大家谈论冷战,仿佛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全然无视二十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亚非拉地区的战火规模。
最近我在老挝办理签证,有幸参观几处博物馆,它们以政府视角记述那段岁月。纪念碑铭刻着内战的胜利,历时十六年,而对方是美国撑腰的保皇党。与邻国柬埔寨奉行“千禧年信仰”不同,老挝很快就开始效仿中国的市场经济。这种灵活使他们得以长期执政,也让国民享受了至今已延续数代的和平。更重要的是,他们避免陷入那种不可言说的残酷。这种残酷源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极其狭隘的生存方式。最惨烈的结局也许没有出现,但不容忽视的是,战争遗留的数百万枚未爆弹仍遍布全国。土地同我们的身体一样,铭记着伤痕。

图:作者拍摄
上世纪 90 年代到千禧年间,我成长过程中,东南亚正全速挣脱战火纷飞的过去。我们放任像波尔布特、苏哈托这样大屠杀主谋相对平静地度过晚年,而年轻一代则热切地建设蓬勃新经济,塑造了今日东南亚的面貌——7-11 便利店、东盟领导人握手合影、天价旅游区、阶层跃升的梦想。政变初期某天,记得我曾对朋友说:我们算幸运了,一直生活在饱经战火的国度,直到三十多岁才真正体会战争的残酷。
但愿缅甸只是个例,愿我们的邻国朋友永远不必重历往昔的暴力。写下这段话时,我听见心底质疑的声音:“这希望是否太天真?”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地缘政治曾将这片区域卷入无谓的战争,而当今的地缘格局同样让我不安。
我想要记住那些根本无需担忧暴力和伤痛的时光。我想我从未找到合适的方式来铭记失去的感觉。如何纪念失去的至亲,我仍很困惑。
我失去过很多。女性长辈相继离世——母亲、祖母、姑姑。随年岁增长,与父亲的关系日渐疏离。一段失败的婚姻让我身心俱碎。政变后,对国家的集体期望也破灭了。最近我开始重新接受心理治疗,上周六,我进行了一次特别沉重的心理咨询,我必须直面悲伤,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为生命中至亲离世的伤痛,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释怀。我不知道该如何悲伤,也没有机会弄清楚。对我来说,生活总是意味着拾起碎片、继续前行、重建一切,而非沉湎于痛苦,或设法实现逝者的期望来减轻愧疚。直到心理治疗我才恍然明白,他们的愿望或许是我免受煎熬。

图:(缅)Khin Thethtar Latt (Nora)
当我将个人境遇推及缅甸的几百万同胞时,那是一种难以估量的集体伤痛。我们该如何消化这一切?是在尚未失去一切的旧日时光里寻找欢愉?还是在缅怀逝者时获得安宁?抑或营造一个既放松又欢愉的未来?我逐渐意识到,若不懂得在释怀和铭记之间取得平衡,便无法走出暴力循环泥沼,因而发展不出更有生机的未来。
选择未来
二月底,我在台北参加一场会议,期间常在阴郁的天空下久久漫步。与会者大多来自世界各地从事数字权利工作的民间团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绝望感。我持续数小时漫步台北街头,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是《上帝之国》—— 创作型歌手埃塞尔·凯恩(Ethel Cain)深受美国南方哥特风影响的曲子。 朋友们叮嘱我“好好享受,珍惜当下”。但我似乎在提前哀悼一个刚刚踏足的地方,又或许我是在为自己的故乡悲伤,因为我从未在尚有机会时真正领略它的美好。我们所爱的一切,不也总是这样吗?也许我还在为整个世界的现状而悲伤。埃塞尔的歌词如倒转的塞壬之歌[1] ,在脑中回荡,将我引向一个严肃的真相——我们孩子成长的环境,资源只有我们的一半,背负从尘土中重建一切的重担,这似乎已成定局。

图:作者拍摄
我不怎么了解台湾历史,访问台湾那周,碰巧赶上了他们纪念194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的日子。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它与我一直在探究的“中国革命”非常契合,所以借此机会自学了一番。
台湾岛历经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战败后,被交还给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非常复杂,他们从未与大陆建立起完全的归属感,而日治时期经历蓬勃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繁荣程度堪称亚洲独有。日本在亚洲其他殖民地暴行累累,却将台湾打造为“模范殖民地”,为岛民带来了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就业机会以及新铸就的台湾身份认同。战后仓促将台湾交还给大陆那个摇摇欲坠、充满戒心的国民党政府后,经济随即暴跌,许多台湾人陷入绝望。当局与民众间的紧张关系急剧升级,俨然一只蓄满火药的木桶,只待一粒火星引爆。
当社会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时,同样的模式便会重演。仅仅一个选择、一次反抗的举动,便足以引爆局势——突尼斯的小贩,仰光茶馆里一群学生的争执,美国南方公交车上拒绝服从种族隔离给白人让座的女子,皆是如此。1947 年 2 月 28 日,台湾贩卖私烟的寡妇与为难她的一队警察对峙,围观群众试图干预,某士兵惊慌开枪,公众怒火随之沸腾,接着便是高度戒备的镇压。
据估计,后续冲突中死亡人数高达 2.8 万。国民党士兵刚经历苦战,自身也饱受创伤,却开始在台湾无差别射杀平民。持续数周的残酷镇压最终演变为长达近四十年的戒严体制,直至 1987 年才告终结。这段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夜半敲门便意味着与至亲永别。国民党政府疑心重重,而统治着的这片土地,民众忠诚度不一。可悲的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方式,对我们这些曾在威权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来说,太懂了。被恐惧吞噬的人,只会用恐惧来统治。
都说受过伤的人,最会伤人。
从自身经历中我体会到,无论有意无意,都难免伤到他人。有时生活所迫,做出艰难抉择,伤害在所难免;有时正因为逃避现实、不敢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带来伤害;有时则是出于对受伤的恐惧而先发制人。但我愿意相信······不,我确信,当你直面他人的苦楚时,一定会生出一丝共情,一定会想到,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应想办法尽量避免。我所希望的,是不要以虐为乐。
整整一年,我们眼睁睁看着加沙种族灭绝实时直播。但是全球民众非但没有觉醒、反省世上所纵容的暴行,反而通过投票进一步支持独裁。我们正加速坠落,与共情完全背道而驰。
成长的过程中,我被灌输了一套非常西方的价值观教育,对此也质疑过,但现在回想起来质疑得远远不够。我曾深信,西方民主国家拥有不可撼动的强大制度。个体或许非理性,蛊惑人心的政客可能占据舞台,但这些西方民主国家总有强大的制度力量将一切拉回自由主义的、基于规则的常态。我们只需揭露社会弊病,凝聚政治意愿来修正它们。权力狂人的政变,只会发生在那些民主制度的神奇力量尚未成熟的国度。
我们正认识到,这多少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因为规则体系的真相在于,当人们决定破坏规则时,这些规则就会像枯枝般易折。我们既不是机械的自动装置,也不是计算机代码——这些制度依赖于人类在每个决定中对未来的选择。我们无法在冷静从容中,或以深思熟虑、沉着稳健的方式选择。相反,我们在身体陷入恐慌时选择,在内心恐惧最深、苦痛幻象难以承受时选择,在羞耻感的灼烧下选择。我们选择那些胜算渺茫的“终极豪赌”。我们一再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却始终不敢自我审视——在这样的状态下选择。未来的选择,早已被自己刻意铭记或遗忘的过去所铸造。
所以,也许我们并非在以虐为乐,只是朝施虐的深渊走了太远,走到它的边缘,而洞口又敞得太开,于是忍不住一瞥。也许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就这样坠落,将自我的其他维度抛之脑后。所谓“平庸之恶”[2],就是这最后一步的坠落。
不过,或许勇气也不必如此深刻。“平庸之勇”又如何?意味着什么?我来解释。
平庸之勇
我依然相信制度,但不再迷信那些被我们用白纸黑字写下后又遗忘其规则的制度,幻想它们能超然于人类而存在。我相信这样的制度:它总使我们自发地承担责任,肯定我们的能动性。一个制度能否像一件现代艺术品那样,邀请观看者赋予其完整的意义?一个制度能捕捉到多少身处音乐会中的感觉?每个参与者都沉浸在合唱中,齐声唱出自青春岁月便铭刻于心的歌词。此刻你正体验一种极度私人的共鸣,恰恰因为与人群融为一体。
政治不过是我们共同从事的事业。关键在于,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一种全体共识的境界,仿佛剩下的只需敲定细枝末节。正如艺术与音乐是人类不懈努力的永恒源泉(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创作、构建,并沉醉于它们赋予生命摄人心魄的美),我们同样也不会停止政治活动。
我二十多岁的自我认同,完全是个沉迷经济政策的书呆子形象,深信政治不过是无知之徒的聒噪,他们总为自己根本不懂的事争吵不休。而政策讨论才是深刻、敏锐头脑的智慧交锋,他们在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直到又历经十年光阴,见证社会运动的运作机制,法律如何诞生又如何沦为治理工具,哪些议题被聚焦哪些被漠视后,我才明白,我们的政治程序从设计之初——或者说早被劫持——就是为了规避真正的政治。这十年同样让我饱尝了苦痛、失去、希望、背叛与团结的滋味,意识到那些创伤的烙印,对于我和所有人的每个生命抉择,都影响深远。
我们一直都在勇敢做出这些选择。我们每天都行使自己的主动权。关键在于跳出思维定式,别以为构想的一切都被简化成一份乏善可陈的选项清单。当有人递给你这样的清单时,要把它撕得粉碎,然后去创造、想象、联结并确证:你存在于世,本就是一个真正的行动者。
台湾旅行期间,我专程去 G0v(读作“Gov-Zero”)举办的“黑客松”[3]朝圣,之前倾慕已有十年。这是一个由技术专家组成的社群,每到周末就聚在一起,共同开发热衷的社会议题。
有人自发研究海底互联网电缆网络的脆弱性;另一组人正在详细登记全台公立医院信息,录入开源地图平台 Open Street Map;还有人在编代码,试图从政府预算报告中提取有价值的数据;一位乌克兰访客则分享俄乌战争爆发时,他们如何动员起来为几千名儿童提供在线教育。他们正是我的同类,我最能共鸣的伙伴。世界各地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日复一日默默努力,以微小的突破构筑更美好的未来。
G0v 的成立在 2014 年,当时台湾遭遇重大瓶颈。学生们占领议会二十三天,五十万人上街声援学生。占领运动以“彻底透明”为原则,议事过程全程直播,讨论记录得到细致地数字化存档,这种开放性有效防止了网络水军和虚假信息的干扰。来自 g0v 的技术专家成为运动的技术支柱,他们搭建直播系统、协调文件归档、设计协作机制,让全台民众得以实时观看并参与。此后的十年间,台湾通过数字技术,一次又一次扩大民众参与,这个话题值得另撰长文详述。
这种集体行动恰恰解释了我所说的,我相信那些让我们确证自身能动性的制度。学生们自称“示范者”而非“抗议者”,因为他们正在示范另一种可能,更优的解决方案。这是将愤怒转化为乐观,被动转化为团结,以服务同胞的精神搭建共识基础。当存在这样一种有机自发的制度,激发你展现最好的自我时,勇气便不再是什么伟大的英雄壮举,而是自然的本能反应。
多年以前,我在本科论文中研究了集体行动的模式。在文献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核心规律:主体能动性始终是运动的基石。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南方黑人教堂周围形成紧密社区,为人们提供滋养的沃土。在八十年代萨尔瓦多内战中,起义者小规模集体行动的成功,使参与运动本身成为一种愉悦而自我确证的行动。
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认为由于过去的伤痛,未来早已注定,局限为一座小岛,仅存些许安稳空间,周围环绕着不敢涉足的深渊。这种信念会导致我们陷入瘫痪,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1975 年后的老挝与柬埔寨形成鲜明对照——当权者选择放大历史创伤还是彻底挣脱枷锁,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明确一点,我并非倾心于老挝体制,但其领导人与波尔布特一样,都是在战争中磨砺出的丛林游击战士,但他们没有选择延续数十年来浸透日常的暴力循环。施虐大门敞开,但他们并未踏入。
回到缅甸这个话题,我们要感谢那些在数字安全领域不懈努力的伙伴,正因为他们打下基础,才让全国人民一夜之间就普及了加密通讯软件。在 2010 年代,无数团体、倡议组织和社群都觉得自己可以在未来有所作为。他们只是尽职工作、投身所爱之事,却为日常的勇敢之举筑起基石。
这是一次耗尽心力却又必要的梳理,理清了过去几月内心翻涌交织的想法和感受。我很庆幸写下那首诗,并坦然接纳了汹涌而来情绪。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一直想表达什么。诗的结尾我透露了一条讯息:那些试图控制我们的人,请明白,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译者介绍: Jiaxi, @伦敦。念人类学。目前研究泰缅克伦部落的说唱音乐,也拍片。
注释:
- 希腊神话中的海妖,用歌喉使得水手倾听失神,船只触礁沉没。——译注 ↩︎
- 源于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指普通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下无思想、无意识地犯罪。——译注 ↩︎
- 黑客松(Hackathon) 是一种在限定时间内集中协作的编程活动,通常由开发者、设计师、创业者或相关领域爱好者组队参与,旨在通过高强度协作、快速开发出创新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或产品原型。其名称由 "Hack"(指创造性编程)和 “Marathon”(马拉松)组合而成,强调持续专注的协作精神。——译注 ↩︎
- 封面图:Khin Thethtar Latt (Nora)-《失去身份(Losing Identity Series 6)》 ↩︎